| [1] |
杨东,黄尹旭. 元平台:数字经济反垄断法新论[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36(2):117-127.
|
| [2] |
方兴东. “互联互通”解析与治理——从历史维度与全球视野透视中国互联网深层次问题与对策[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50(5):1-13.
|
| [3]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EB/OL]. 中国政府网(2019-08-08)[2022-09-14].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8/08/content_5419761.htm.
|
| [4] |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EB/OL]. 中国质量新闻网(2021-10-29)[2022-12-23]. https://www.sac.gov.cn/cms_files/filemanager/samr/www/samrnew/hd/zjdc/202110/t20211027_336137.html.
|
| [5] |
工信部. 限期解除链接屏蔽[EB/OL]. 中国经营网(2021-09-12)[2022-09-14].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0681979368402053&wfr=spider&for=pc.
|
| [6] |
唐仁敏,陈思锦. 把握平台经济发展规律建立健全平台经济治理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同志就《关于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答记者问[J]. 中国经贸导刊,2022(2):36-37.
|
| [7] |
殷继国,唐渊明. 论互联网平台互联互通的法治保障[J]. 竞争政策研究,2022(4):17-33.
|
| [8] |
高薇. 平台监管公用事业理论的话语展开[J]. 比较法研究,2022(4):171-185.
|
| [9] |
邓志松. “互联互通”的行业监管、竞争规制与多元价值平衡[J].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37(8):46-55,95.
|
| [10] |
ARMSTRONG M. Network interconnection in telecommu-nications [J]. The Economic Journal,1998,108(5):545-564.
|
| [11] |
高薇. 美国平台公用事业管制的理论及其发展[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5(5):76-87. doi: 10.3969/j.issn.1000-579X.2022.05.009
|
| [12] |
刘权. 平台互联互通的困境与法治回应[J]. 中国应用法学,2023(3):54-64.
|
| [13] |
刘继峰,张佳红. 平台封禁行为的竞争法分析[J]. 当代经济科学,2023,45(1):17-28.
|
| [14] |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市场监督总局发布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行政处罚决定[EB/OL].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22-07-12)[2022-09-14].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7930658507481853&wfr=spider&for=pc.
|
| [15] |
刘权. 论互联网平台的主体责任[J].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2,25(5):79-93. doi: 10.3969/j.issn.1008-4622.2022.05.006
|
| [16] |
李希梁. 反垄断监管与事前监管——互联网平台监管模式的二元建构[J]. 交大法学,2023(2):89-103.
|
| [17] |
张浩然. 事后反垄断与事前管制——数字市场竞争治理的范式选择[J]. 河南社会科学,2021,29(8):37-48.
|
| [18] |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美团行政指导书全文公布 [EB/OL]. 北京日报(2022-08-31)[2022-09-14].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8/31/content_5634278.htm.
|
| [19] |
李希梁. 平台互联互通的法理问题与监管限度[J]. 知识产权,2023(6):107-126. doi: 10.3969/j.issn.1003-0476.2023.06.006
|
| [20] |
王帅. 作为必需设施的超级平台及其反垄断准入治理[J]. 北方法学,2021,15(5):148-160.
|
| [21] |
孔祥俊. 论互联网平台反垄断的宏观定位——基于政治、政策和法律的分析[J]. 比较法研究,2021(2):85-106.
|
| [22] |
陈兵,赵青. 反垄断法下互联网平台“封禁”行为适法性分析[J]. 兰州学刊,2021(8):64-75.
|
| [23] |
叶明,贾海玲. 双重身份下互联网平台自我监管的困境及对策——从互联网平台封禁事件切入[J]. 电子政务,2021(5):12-20.
|
| [24] |
杜颖,魏婷.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中的商业道德认定问题研究[J]. 知识产权与市场竞争研究,2020(1):109-128.
|
| [25] |
林婧,陈琳. 网络广告屏蔽行为性质认定中利益衡量方法的适用改进[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6(4):79-87.
|
| [26] |
焦海涛. 平台互联互通义务及其实现[J]. 探索与争鸣,2022(3):118-128,179.
|
| [27] |
李世刚,丁裕睿. 大型数字平台规制的新方向:特别化、前置化、动态化——欧盟《数字市场法(草案)》解析[J]. 法学杂志,2021,42(9):77-96.
|
| [28] |
邹开亮,王馨笛. 敏感个人信息保护视阈下平台企业数据合规制度要论[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0(2):87-93.
|
| [29] |
时建中,吴宗泽. 作为反垄断救济措施的数字平台互操作义务[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42(1):108-125.
|
| [30] |
张钦昱. 数字经济反垄断规制的嬗变——“守门人”制度的突破[J]. 社会科学,2021(10):107-117.
|
| [31] |
杨东,侯晨亮. 论平台“封禁”的反垄断规制——以社交平台为研究对象[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52(4):50-66.
|
| [32] |
刘乃梁,吕豪杰. 平台经济互联互通:规制源流、进路与中国方案[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2(4):35-46.
|
| [33] |
陈兵,林思宇. 数字经济领域数据要素优化配置的法治进路——以推进平台互联互通为抓手[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2,24(3):123-138.
|
| [34] |
侯利阳. 平台反垄断的中国抉择:强化反垄断法抑或引入行业规制?[J]. 比较法研究,2023(1):32-48.
|
| [35] |
高志宏. 公共利益:基于概念厘定的立法导向与制度优化[J]. 江西社会科学,2021,41(10):183-193.
|
| [36]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J].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2015(Z2):6-19.
|

 点击查看大图
点击查看大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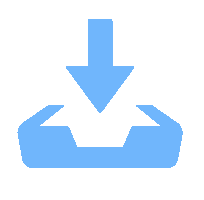 下载:
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