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larization” of Digital Employment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s
-
摘要: 数字就业的“极化”现象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高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增加而中等技能劳动力就业减少,这让“机器换人”与“机器创造就业”的观点互为争论,学界对此也结论不一、对“极化”的机制也未揭示全貌。文章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综合梳理与分析,呈现相关问题的研究动态与前沿,借鉴已有研究经验,凝练“极化”背后的机制与形成路径,用于分析我国就业与收入极化的现状。文章通过分析提出了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的就业作用框架模型,其中产品市场起到引致劳动力需求的作用,要素市场则搭建数字技术与“信息—劳动—资本”传统三要素模型,并引入“技术—数据要素”模型。认为技术作用于信息、造成信息垄断与信息不对称,将高中技能劳动者留在劳动力市场,更多将低技能劳动者排除在市场之外;技术作用于劳动,直接产生就业极化,表现为对劳动就业的创造效应与破坏效应所形成的总效应;技术作用于资本,则劳动与资本的谈判力决定了二者如何分配所创造的收入。数据要素依附数字劳动,易于形成高技能数字劳动“被强化”、中低技能数字劳动“被弱化”的“单极化”结果。最终,就业是否极化以及极化的程度,取决于传统要素、数字要素与产品市场共同博弈的结果。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polarization” in digital employment is widespread around the world. The employment of high- and low-skilled labor increases and the employment of middle-skilled labor decreases, which leads to the controversy between the views of “machine-replacement” and “machine-created employmen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come to different conclusions on this issue, and has not revealed the full picture of the "polarization" mechanism.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s and frontiers of relate issues by comprehensively combing and analyzing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draws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experience, and condenses the mechanism and formation path behind the “polarization”, which is used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mployment and income polariz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proposes a framework model of factor market and product market in employment, in which the product market plays the role of inducing the labor demand, and the factor market builds the traditional three-factor model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labor-capital”, and introduces the “technology-data-factor” model. The role of technology in information generates information monopoly and information asymmetry, which includes high-skilled workers in the labor market and excludes low-skilled workers from the market. Besides, the role of technology in labor directly generates employment polarization,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total effect of creating and destroying labor and employment. Additionally, the role of technology in capital determines the negotiation power of labor and capital in how to distribute the income created by the two. Data factors are dependent on digital labor, which is easy to form the “unipolar” result of “strengthened” high-skilled labor and “weakened” middle- and low-skilled digital labor. Finally, the magnitude of employment polarization depends on the result of the joint game between traditional factors, digital factors and product markets.
-
Key words:
- digital employment /
- polarization /
- technological progress /
- digital data /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表 1 技术进步与劳动力就业关系的相关理论基础
理论基础 主要内容 具体理论与模型 提出或代表学者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以提高劳动力的技术进步为假设前提构建模型,从资本与
劳动力比率入手集中分析均衡(稳态)增长路径索洛模型
索洛—米德模型
内生增长模型索洛(1956);索洛和米德(1960);罗默(1990)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 价值决定价格,价格围绕价值波动,数据要素的价格(等同参与收入分配)取决于数据要素本身的特性以及与要素需求方的谈判力量;数字劳动以多种方式参与收入分配 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1975);德斯(1999);克里斯汀.福(2014) 信息不对称与信息垄断 数字技术产生的信息垄断与不对称导致就业结构性差异 信息技术与市场租金理论 古勒等(2017) 技术偏向理论 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促发高技能劳动就业增加,技能退化型技术进步促发低技能劳动就业增加 技能偏向型技术理论
技能退化型技术理论
任务偏向型技术进步伯曼等(1994);奥托等(1998;2003);如塞尔等(2000);
艾斯毛格鲁(1998)技术创新理论 技术进步开发新产品、新工艺,使得经济中出现新的产业部门,影响就业结构的变化与就业再分配 开创性地强调工厂间就业的异质性 皮安他(2001);戴维斯和海万格(1992)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整理。 -
[1] BRYNJOLFSSON E & MCAFEE A. Race Against the Machine:How the Digital revolution is Accelerating Iinnovation,Driving Productivity,and Irreversibly Transforming Employment and the Economy[M]. Lexington:Digital Frontier Press,2012. [2] ACEMOGLU D & RESTREPO P. Robots and jobs:Evidence from US labor market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20,128(6):2188-2244. doi: 10.1086/705716 [3] 程承坪,彭欢. 人工智能影响就业的机理及中国对策[J]. 中国软科学,2018(10):62-70. doi: 10.3969/j.issn.1002-9753.2018.10.008 [4] 潘丹丹. 人工智能的就业反极化效应研究[J]. 现代经济探讨,2019(12):25-31,65. doi: 10.3969/j.issn.1009-2382.2019.12.006 [5] 王永钦,董雯. 机器人的兴起如何影响中国劳动力市场?——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J]. 经济研究,2020,55(10):159-175. [6] AUTOR D H,LEVY F & MURNANE R J. The skill content of recent technological change:An empirical exploration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3,118(4):1279-1333. doi: 10.1162/003355303322552801 [7] 杨虎涛,冯鹏程. 去技能化被证伪了吗?——基于就业极化与技能溢价的考察[J]. 当代经济研究,2020(10):2,50-63,113. [8] 杜传忠,许冰. 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及中国的对策[J]. 社会科学战线,2018(2):68-74. [9] AUTOR D H. Polanyi’s paradox and the shape of employment growth[J/OL].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4-09) [2023-12-01]. https://www.nber.org/system/files/working_papers/w20485/w20485.pdf. [10] FINNIGAN D. Robots and automation may not take your desk job after all[J/OL].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6-11-22)[2023-12-01]. https://hbr.org/2016/11/robots-and-automation-may-not-take-your-desk-job-after-all. [11] WRIGHT E O & DWYER R E. The patterns of job expansions in the USA:A comparison of the 1960s and 1990s [J]. Socio-Economic Review,2003,1(3):289-325. doi: 10.1093/soceco/1.3.289 [12] BERNARD A & JONES C. Technology and convergence [J]. The Economics Journal,1996,106(437):1037-44. doi: 10.2307/2235376 [13] AGHION P & HOWITT P. Growth and unemployment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4,61(3):477-494. doi: 10.2307/2297900 [14] DOWRICK S & ROGEST M. Classical and technological convergence:Beyond the solow-swan growth model [J]. Oxford Economic Papers,2002,54(3):369-385. doi: 10.1093/oep/54.3.369 [15] 孔艳芳,刘建旭,赵忠秀. 数据要素市场配置研究:内涵解构、运行机理与实践路径[J]. 经济学家,2021(11):24-32. [16]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7] DIETL H. Selling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J]. Hitotsubashi Journal of Commerce and Management,1999,34(1):1-14. [18] 初传凯.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视域下数字劳动探究[J]. 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21,23(6):30-37. [19] 徐少俊,郑江淮. 信息化引致中国劳动力市场极化了吗——多层次技能深化假说与检验[J]. 经济问题探索,2020(7):157-167. [20] LEE N & CLARKE S. Do low-skilled workers gain from high-tech employment growth? High-technology multipliers,employment and wages in Britain. Research Policy,https://doi.org/10.1016/j.respol.2019.05.012. [21] HUNT J & NUNN R. Is employment polarization informative about wage inequality and is employment really polarizing? [R]. Cambridge: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19. [22] ACEMOGLU D & RESTREPO P. Low-skill and high-skill automation [J]. Journal of Human Capital,2018,12(2):204-232. doi: 10.1086/697242 [23] 纪雯雯. 数字经济与未来工作[J].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7,31(6):37-47. [24] 唐永,蒋永穆. 产业结构服务化会导致中国劳动力市场极化吗?[J]. 经济评论,2022(2):51-69. [25] 江永红,张彬,郝楠. 产业结构升级是否引致劳动力“极化”现象[J]. 经济学家,2016(3):24-31. [26] 陈仪,李亚楠. 全球趋势背景下我国劳动力市场就业极化问题初探[J]. 新视野,2023(5):105-113. [27] 程旭,睢党臣. 人工智能时代就业信息不对称分析及规避策略[J]. 宁夏社会科学,2021(1):120-127. [28] 邱玥,杜辉. 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研究[J].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9,33(3):5-14. [29] ERIKSSON C. Is there a trade-off between employment and growth? [J]. Oxford Ecnomics Papers,1997,49(1):77-88. doi: 10.1093/oxfordjournals.oep.a028598 [30] 姚战琪,夏杰长. 资本深化、技术进步对中国就业效应的经验分析[J]. 世界经济,2005(1):58-67,180. [31] 蒋南平,邹宇. 人工智能与中国劳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 四川大学学报,2018(1):130-138. [32] 吴清军,陈轩,王非,等. 人工智能是否会带来大规模失业?——基于电商平台人工智能技术、经济效益与就业的测算[J]. 山东社会科学,2019(3):73-80. [33] ACEMOGLU D. Technical change,inequlity and the labor market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2,40(1):7-72. doi: 10.1257/jel.40.1.7 [34] KATZ L F. Changes in the wage structure and earnings inequality[J].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1999(3):1463-1555. [35] AUTOR D H,KATZ L F & KRUGER A B. Computing inequality:have computers changed the labor market?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ocs,1998,113(4):1169-1213. doi: 10.1162/003355398555874 [36] 宋冬林,王林辉,董直庆. 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存在吗?——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 经济研究,2010(5):68-81. [37] 王君,张于喆,张义博,等.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步影响就业的机理与对策[J]. 宏观经济研究,2017(10):169-181. [38] 孙早,侯玉琳. 智能化推动就业结构深刻变革[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7-24(04). [39] 郝楠,江永红. 谁影响了中国劳动力就业极化?[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17,38(5):75-85. [40] 王晓霞,白重恩. 劳动收入份额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进展[J]. 经济学动态,2014(3):107-115. [41] 傅晓霞,吴利学. 偏性效率改进与中国要素回报份额变化[J]. 世界经济,2013,36(10):79-102. [42] AUTRO D & SALOMONS A. Is automation labor share-displacing? Productivity growth,employment,and the labor share[J].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2018(1):1-63. [43] 姜耀东. 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数字劳动的价值走向——基于马克思整治经济学的批判[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6):108-113. [44] 于苗苗. 人工智能时代人力资本对现代服务业就业的影响研究[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6(2):82-88. -

 点击查看大图
点击查看大图
表(1)
计量
- 文章访问数: 1593
- HTML全文浏览量: 225
- PDF下载量: 44
- 被引次数: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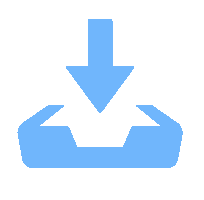 下载:
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