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 Re-interpretation of Modality Types
-
摘要: 系统功能语言学将情态定义为介乎肯定与否定两极之间的意义域,将情态归入人际元功能。但对情态系统的描写仍有以下问题:情态的类型划分简单模糊;情态的主客观描述不一;未考虑情态元功能多样性。理论与系统的模糊导致了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框架的情态描述缺乏跨语言方面的统一性。解答以上存疑,有助于全面了解情态的本质,也为情态的类型学描述提供更加完整的框架。本研究发现,情态可以根据两个参数区分三种类型;“主观性”这一术语应区分三种用法,韩礼德对情态主客观的描述是以说话人参与为前提,体现的是主观范畴内的不同程度的确定性;情态类型及其主客观特征不是绝对的区别,而是沿着人际元功能与概念元功能构成一个连续统。Abstract: In SFL, modality refers to the semantic space between positive and negative poles, and it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interpersonal resource.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the systemic functional description of the modality system. For example,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modality system manifests simplicity and vagueness; discussions of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 of modality appear contradictory; and the metafunctional diversity of the modality system is ignored. The ambiguity of the theory and system leads to inconsistent typological accounts of modality. In resolving these problems, we contribut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modality, thereby providing an integrated typological framework for its descrip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modality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major types based on two parameters.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meanings given to the term “subjectivity”, and Halliday’s account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modality assumes speaker’s involvement and reflects varying levels of commitment on the part of the speake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modality types and their distinction in terms of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 are gradual rather than categorical. They form a continuum along the cline of interpersonal and ideational metafunction.
-

图 1 情态类型的系统网络图

图 2 元功能视角下的情态连续体
-
[1] HALLIDAY M A K. Functional diversity in language as seen from a consideration of modality and mood in English [J].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1970, 6(3):322-361. [2] 杨曙,李妹惠. 汉语情态研究述评:回顾、反思、趋势[J].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8(2):179-184. [3] HALLIDAY M A K & Matthiessen C M I M. Halliday’s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4th ed.)[M]. London: Routledge, 2014. [4] KADOOKA, K-I. A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English and Japanese modality systems[C] // KADOOKA K-I. Japanese Mood and Modality in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Theory and Application. Amsterdam: Benjamins, 2021: 101-132. [5] 张玉波,杨炳钧. 小句极性的元功能归属[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19,51(2):225-238,320. [6] LYONS J. Seman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7] BYBEE J L. Morphology: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Meaning and Form[M]. Amsterdam: Benjamins, 1985. [8] VAN DER AUWERA J & PLUNGIAN V A. Modality’s semantic map [J]. Linguistic Typology, 1998, 2(1):79-124. [9] PALMER F R. Mood and Modality (2nd ed.)[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0] 赵春丽,石定栩. 语气、情态与句子功能类型[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11,43(4):483-500,639. [11] 杨曙,常晨光. 情态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考量[J]. 外语学刊,2011,160(3):27-31. doi: 10.16263/j.cnki.23-1071/h.2011.03.019 [12]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 London: Arnold, 1985. [13]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 )[M]. London: Arnold, 1994. [14] HALLIDAY M A K & Matthiessen C.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3rd ed. )[M]. London: Arnold, 2004. [15] PERKINS M R. Modal Expressions in English[M]. London: Croom Helm, 1983. [16] COATES J. The Semantics of the Modal Auxiliaries[M]. London: Croom Helm, 1983. [17] WRIGHT G H V. An Essay in Modal Logic[M].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1951. [18] BYBEE J L, PERKINS R D & PAGLIUCA W.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19] JESPERSEN O. 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24. [20] PALMER F R. Mood and Modalit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21] VERHULST A,DEPRAETERE I & HEYVAERT L. Source and strength of modality:an empirical study of root should,ought to and be supposed to in present-day british English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3, 55(11):210-225. [22] FILLMORE C J. The case for case[C] // BACH E & HARMS R T. Universals in Linguistic Theor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8: 1-88. [23] FOLEY W A &VAN VALIN R D. Functional Syntax and Universal Gramma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24] HENGEVELD K. Layers and operators in functional grammar [J].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989, 25(1):127-157. doi: 10.1017/S0022226700012123 [25] VERSTRAETE J C.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modality:interpersonal and ideational functions in the English modal auxiliary system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1, 33(10):1505-1528. doi: 10.1016/S0378-2166(01)00029-7 [26] HOYE L. Adverbs and Modality in English[M]. London: Longman, 1997. [27] NUYTS J. Subjectivity as an evidential dimension in epistemic modal expression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1, 33(3):383-400. doi: 10.1016/S0378-2166(00)00009-6 [28] NUYTS J. Notions of (inter)subjectivity [J]. English Text Construction, 2012, 5(1):53-76. doi: 10.1075/etc.5.1.04nuy [29] 常晨光. 英语中的人际语法隐喻[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7):6-8. doi: 10.3969/j.issn.1004-6038.2001.07.003 [30] PALMER F R. Modality and the English Modals[M]. London: Longman, 1990. [31] NUYTS J. Analyses of the modal meanings[C] // NUYTS J & AUWERA J V 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ality and Moo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31-4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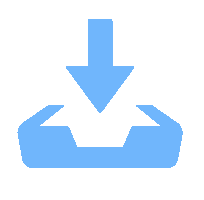 下载:
下载:


